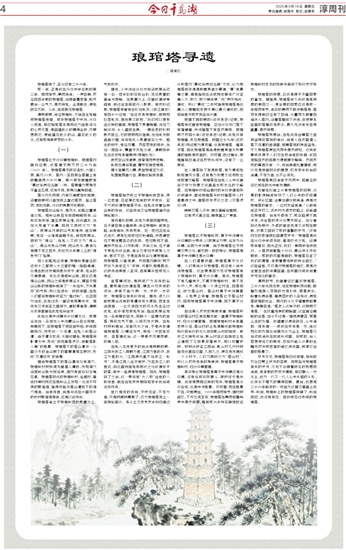徐建仁
琅琯塔倒了,至今已有二十六年。
那一年,正是我在汾口中学任教的第二年。梅雨季节,暴雨连连。一声巨响,历经四百余载的琅琯塔,如同垂暮老者,耗尽最后一丝气力,轰然倒地。尘烟散去,满地砖石瓦砾。从此,世间再无琅琯塔。
清明假期,途经琅琯岭,不由自主地踏进琅琯塔废墟。或许琅琯塔于中洲、汾口人而言,早已超越塔本身而成为血脉深处的心灵灯塔,是回望故乡的精神坐标,只要想起它,便能望见故乡的山,望见故乡的水,还有那魂牵梦萦的乡愁。
(一)
琅琯塔位于汾口镇琅琯岭。根据塔内碑刻记载,该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琅琯塔属于砖石结构,六面七层,高约39米。塔内一至四层各塔壁上有砖雕造像六十六尊。第六层东南壁嵌有“募成华表纪名碑”一块。塔腰檐为菱角牙子叠涩五层,逐渐外挑,转角处翼角起翘。
塔分内外两层,内有双道螺旋式楼梯,沿着楼梯可以盘旋而上直达塔顶。登上塔顶,凭栏远眺,汾口的美景尽收眼底。
琅琯塔依山临水,是风水、战略位置俱佳之地。梅岭山脉自东向西蜿蜒而来,山势逐渐变缓,直至武强溪滩,远远望去,犹如大象垂下长鼻,因而又被称之为“象山”。武强溪对岸的山气势雄伟,岩石峥嵘,宛如一头雄狮盘踞于此,俯视武强溪,被称为“狮山”,当地人又称之为“狮头山”。狮山与象山对峙,两山夹水,最窄处相隔不足三百米,形成风水学意义上的“狮象守门”格局。
而从战略地位来看,琅琯岭是曾经的遂安十二都进入十三都的唯一陆路通道,也是古时遂安通向徽州休宁、歙县、屯溪的交通要道。东北边是梅岭山脉,西北边是狮山山脉,两山之间是武强溪水,横亘于梅山山脉的琅琯岭就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们都将琅琯岭称至为“难过岭”。也正因为如此,此地过去一直设有军事关卡。相传东汉末年至三国贺齐,唐时黄巢军、清朝太平军都曾在此地屯兵驻守。
此地也是中洲镇与汾口镇水口。武强溪犹如一条游龙从中洲霞山头自北而南,奔腾而下,在琅琯塔下被巨岩所挡,折向西南而行,并形成一个深潭,当地人叫塔山潭。由于潭水较深,水面成碧色,琅琯塔倒影潭水中,形成“仰视高塔凌云,俯瞰塔影入境”的胜景。琅琯塔下的塔山潭与一公里之外的金山脚下的摩臂潭相互映衬,形成“双潭印月”的奇景。
据说琅琯塔下的塔山潭深处有洞穴。琅琯岭村民张虎龙曾潜入谭底,发现洞穴沿梅岭山脉方向延伸,洞内有岩石似石凳石桌。琅琯塔附近的琅琯岭村、仙居村、章姚村等村民还在梅岭山上发现一处深不可测的野猪洞,推测可能与塔山潭底下的洞穴相连。后有传言,说是与远在十里开外的叶村野猪洞相连,应是以讹传讹。
琅琯塔耸立于琅琯岭顶的悬崖之上,气势恢宏。
据传,从中洲往汾口方向沿武强溪边有一条一百余阶的石板台阶,足见悬崖的高耸与陡峭。在悬崖之上,还曾修建凉亭阁楼,供过往客商和行人歇息。有史料记载,琅琯塔旁曾有古松如虬龙。《浙江通志》卷四十六记有:“在遂安县琅琯岭,根柯斑驳若虬龙,相传秦汉时物。”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的画面,琅琯塔下悬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刻,令人望而生畏。一棵古老的松树傲然挺立,它的根柯斑驳陆离,犹如虬龙般盘曲交错,深深地扎入悬崖岩石之中。粗壮的树干,饱经风霜。茂密葱茏的枝叶,犹如一把巨伞,覆盖于天地之间。清朝陈学孔任遂安知县曾赋诗《琅琯松龙》:
寂历空山足避秦,饱餐烟雨养老鳞。
虬枝烂漫将军盖,霜节支离老叟身。
隔水笙簧风入幔,悬岩琅琯玉为邻。
轮菌樾荫垂终古,莫艳成蹊桃李春。
(二)
琅琯塔岿然屹立于琅琯岭数百年,像一位老者,见证周边地域的岁月变迁。至于为何修建琅琯塔于此,当地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些传说又给琅琯塔编织出神秘面纱。
相传春秋时期,此地为吴楚两国界地,伍子胥自楚仓皇奔吴,途经琅琯岭,前有岔路,后有追兵,形势危急。见一老妇正在溪边洗衣,便急忙向老妇打听道路,并恳请老妇不要泄露自己的去向。老妇默而不语,竟毅然投溪,以死践诺。多年之后,伍子胥于吴地功成名就,每念及老妇守诺殉义之举,感怀不已,于是在其投溪处建琅琯庙、筑琅琯塔,以彰其德。然而塔内碑刻“明万历廿九年辛丑冬”字样,与春秋相隔甚远。这段传说虽感人至深,但其真实性却无从考证。
宝塔镇河妖,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语,意即通过修建宝塔,镇压兴风作浪的河妖,使其不能为祸一方,守护一方平安。琅琯塔也有类似传说。据传,很久以前武强溪流域时常遭受洪水侵袭,百姓生活困苦。一位云游四方的风水先生经过此地,他仔细观察地形后,指出武强溪宛如一条奔腾的巨龙,而缺少一座镇龙的宝塔,导致龙气不稳,从而引发灾祸。当地村民听闻后,深信风水之说,于是决定建造琅琯塔,以镇住龙气,保佑一方百姓平安。自塔建成后,这一带果然风调雨顺,政通人和。
当地人流传更多的说法是明朝时期,江西与浙江人同朝为官,江西为官的多,浙江为官的大。“江西满天星不如浙江一轮月”,于是江西人出于嫉妒,为压浙江人的官运,到这里选择地势起伏之处修建许多砖塔,其中一座便是琅琯塔。因此,琅琯塔到了之后,这一带将有“大人物”出世的八卦传言,就在当地市井巷陌和茶余饭后间流传开来。
世代相传的传说,于史无证,不足为信,只是闲闻轶事罢了,仅为琅琯塔笼上一袭神秘面纱。县乡土文史专家余利归通过分析塔内“募成华表纪名碑”文字,认为琅琯塔或许是佛教善男信女募建。“募”有募集之意,通常指向社会或特定群体广泛征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成”表示完成、建成。所以“募成”二字可推测琅琯塔是依靠众人捐赠和支持才得以最终建成的,而非由官方或家族出资兴建。
根据不同时期的《遂安县志》记载,琅琯塔旁边曾有琅琯庵。正如汾口龙门塔下有福谦庵,中洲雁塔下有自然禅院。根据明万历四十年《遂安县志》记载,此地只有琅琯庵,未见琅琯塔。民国三十九年《遂安县志》则记载为昙花庵,也有琅琯塔。庵早于塔,因此琅琯塔是由佛教善男信女所募建的推断是可信的。只可惜,时过境迁,琅琯庵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了一丝痕迹。
古人建塔除了有佛教塔,有为调和地脉而建风水塔,还有是为祈愿文运进取仕途而建文峰塔。琅琯塔在当地人心中也曾将它作为祈愿文运昌盛求取功名的文峰塔。在琅琯岭村和仙居村的余氏宗谱和张氏宗谱中,都将琅琯塔与叶村雁塔并入村居景诗之中,借塔抒发凌云之志。《双塔凌云》诗:
嶙峋双塔入云中,南北高峰古睦同。
应有凌云高士在,腾身直上广寒宫。
(三)
琅琯塔位于琅琯岭顶,属于中洲镇与汾口镇的分界点,以武强溪为界,溪东为汾口镇,溪西为中洲镇。由于琅琯塔位于两镇交界之处,曾引起一时的争论,琅琯塔是属于中洲镇还是汾口镇?
在人们潜意识里,琅琯塔属于汾口镇。人们常说汾口琅琯塔,而没有人说中洲琅琯塔。这主要是因为紧邻琅琯塔有个琅琯岭村,属于汾口镇。其实,琅琯塔下有几幢房子,不属于琅琯岭村。虽不足十户人家,却也是一个独立村庄,因塔而名,称为塔山村。塔山村属于中洲镇管辖。从地界上来看,琅琯塔位于塔山村内,因而琅琯塔属于中洲镇,而不属于汾口镇。
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琅琯塔所处的塔山村区域在解放前一直属于琅琯岭村,归汾口镇管辖。根据琅琯岭村余其章老师介绍,塔山村的土地是解放前琅琯岭张氏和余氏的女儿嫁到畈头村的陪嫁。新安江水库形成后,畈头村在这些陪嫁土地上建起了几栋黄泥墙房子,用以安置移民。移民迁移至江西后,畈头村几户村民陆续迁居在这里,久而久之,便逐渐发展成一个小村子,人们习惯称之为“塔山村”。所以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讲,琅琯塔属于琅琯岭村,归汾口镇管辖。
其实争论琅琯塔是属于中洲镇还是汾口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保护好才是关键。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琅琯塔是汾口古迹,也是中洲胜景。只可惜,现在胜景不在,只剩遗址。1999年梅雨季节,据村民回忆,下午三点左右,琅琯塔在暴雨和雷鸣声中轰然倒塌,唯有那大半块石碑被时任琅琯岭村支书的张新书背到了张氏家厅存放。
琅琯塔的倒塌,应该是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据推测,琅琯塔年久失修是其倒塌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因素应该是那一年梅雨季节,连日的暴雨不断冲刷塔身,塔顶本身就已经有了裂缝,大量雨水顺着裂缝渗入塔内,沿着塔壁向下渗透,致使原本坚固的塔壁逐渐软化,最终无法承受自身重量,轰然倒塌。
琅琯塔坍塌后,当地流传出镇塔之宝被盗导致塔倒的奇谈,说有人在夜里潜入塔下深潭的岩洞里,把镇塔用的珠宝盗走,不久琅琯塔便在风雨中轰然倾圮。这类故事或许源于人们对古物消逝的怅惘,试图用超自然的因果为遗憾赋予解释。然而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传说虽寄托着情感,却终究是穿凿附会的臆想,权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不足为信,也不必深究。
琅琯塔虽已消逝于风雨中,但曾经的记忆却在时光中愈发清晰。
我曾在抖音上分享琅琯塔的旧照,泛黄的影像瞬间拨动了人们心中的怀旧情弦。评论区里,往事如潮水般奔涌,满是对琅琯塔的眷恋。一位网友留言道:“从前每年正月初二,去叶村外婆家的路上,总能望见琅琯塔。后来外婆走了,那条路便不再涉足,与古塔的缘分也戛然而止。如今看到这张照片,外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温馨的岁月。”还有网友的思绪被拉回青葱岁月:“琅琯塔是我在汾口中学读书时,春游打卡之地。记得那年春日,阳光正好,我们一群同学结伴而行。从塔顶俯瞰整个汾口,青山绿水尽收眼底。那时的风都是甜的,琅琯塔见证了我们的青春,承载着最纯粹的快乐回忆。”这些留言,不仅是对琅琯塔的追忆,更是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望,在字里行间诉说着岁月深处的眷恋。
清明时节,我循着记忆重返琅琯塔。二十六年光阴流转,站在琅琯岭顶远眺,断壁残垣隐入苍翠的竹海杉林,荒草疯长。踩着长满杂草、铺满落叶的小径走近,满地塔砖堆砌成丘。同行的小儿子望着眼前景象,喃喃自语:“塔怎么这样子的,这明明不是塔。” 在孩童纯净的眼眸里,这座曾经巍峨的古塔,如今不过是一堵爬满青苔、荒草丛生的残墙。我望着这满目砖石,心中涌起一阵怅惘——或许在未来某一天,连这斑驳的残垣也将随风化为尘土,琅琯塔终将彻底消失在时间长河里。到那时,后人若想寻觅它的踪迹,恐怕只能从泛黄的古籍书页中或老者的追忆讲述里,拼凑它往昔的胜景了。
岁月匆匆,琅琯塔早已成废墟,废弃砖瓦也已蒙上岁月的苔痕。而那些与琅琯塔有关的岁月,终究不会随着砖石的坍塌而消逝,其承载的历史与情感,早已融入一方水土,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恒的乡愁,化作永不磨灭的精神图腾。最后,我想用二十六年前写的一句话为这篇文章画上句号:听说,琅琯岭上的琅琯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琅琯塔。